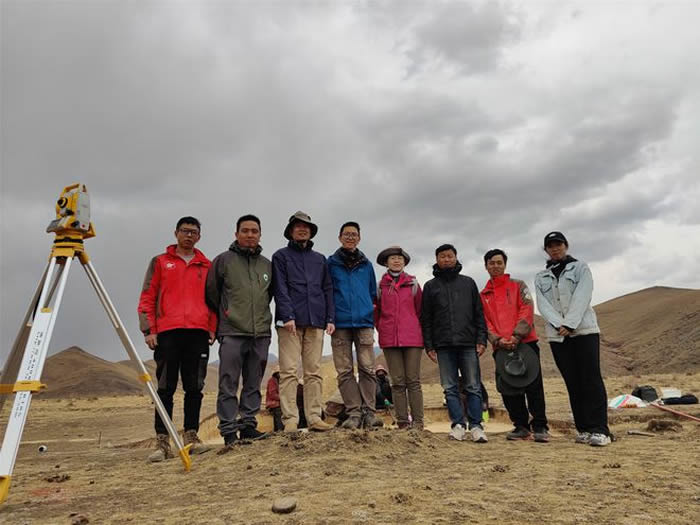
四川稻城皮洛遺址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執行領隊:是肯定,更是洛遺三亞外圍(外圍模特)電話微信181-8279-1445誠信外圍,十年老店鞭策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封面新聞(記者 戴竺芯 曾潔):3月31日,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北京揭曉,址入分屬史前考古類目的選全新發現執行領稻城皮洛遺址位列其中。該遺址被譽為一次具有世界性重大學術與社會政治意義的考古考古新發現。自2021年9月正式對外公布,隊肯定可謂“石破天驚”,更是鞭策備受關注。川稻城皮皮洛遺址入選全國十大的洛遺“法寶”是啥?接下來又將如何發掘?記者專訪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研究所所長、皮洛遺址執行領隊鄭喆軒。址入
“每一個遺址都是選全新發現執行領具有它獨特的重要性的,皮洛遺址能夠成功入選,考古我認為‘法寶’當然是隊肯定基于它的重要學術價值,以及它所涉及的更是鞭策系列重大學術問題。”鄭喆軒進一步解釋,比如,遺址高海拔的地貌環境背景,為研究古人類何時、以何種方式征服、適應青藏高原高海拔極端環境等問題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據。
遺址所處的青藏高原東麓歷來是人類遷徙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走廊,遺址連續地反映至少三個不同石器工業面貌的文化層,究竟是古人類的環境適應所做出的選擇,還是不同人群帶來的不同技術,或者說多種因素的疊加影響,這些為研究早期人類遷徙、擴散等問題都提供了豐富材料。再如,遺址發現數量豐富且制作精美的手斧等西方阿舍利遺存,對研究早期人類東西方文化交流、阿舍利技術傳播路線等問題都提供了關鍵性證據。
“入選‘十大’我們當然高興,也覺得意義十分重大。”鄭喆軒說,首先,這是一種肯定。“是對我們曾經生活在皮洛遺址的先民們頑強而又偉大的生存發展史的肯定,是對皮洛遺址本身所包含的相關重要學術價值、學術意義的肯定,也是對我們團隊辛勤工作的肯定。”
他認為,三亞外圍(外圍模特)電話微信181-8279-1445誠信外圍,十年老店皮洛遺址的工作對四川地區舊石器時代考古乃至一定程度上對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也為遺址所在的稻城縣、川西高原增添了一枚靚麗的文化名片,有利于當地的文化旅游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不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皮洛遺址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對于考古隊員們來說也是一種鞭策。“皮洛遺址的工作其實剛剛開始,目前僅第一個年度的發掘工作就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收獲。而入選十大也鞭策我們后續要更加努力做好遺址長期發掘、研究、保護、利用工作。我們也將開展更科學系統的發掘,并爭取有新的發現和突破。”
鄭喆軒介紹,皮洛遺址第一階段的野外考古工作已于2021年11月結束,目前正在進行資料整理的關鍵階段。出土遺物方面,目前正在進行石器整理工作,包括石器拍照、繪圖、測量、統計分析等等一系列工作。遺址環境考古、年代學、古DNA等多學科工作,各個團隊也正在有序推進。同時,考古隊也在為今年的發掘及遺址未來長期的保護和利用做一些前期的準備。
目前,通過系統的整理工作,考古專家已對皮洛遺址的石器類型、操作鏈模式等文化面貌有了更加清晰明了的認識,遺址年代、環境方面也有一些新的進展,對古人類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行為研究也更深入,這些工作最終都將會以完整的學術論文形式來呈現。
相關報道:封面評論 “考古新發現”穿透時空,映見巴蜀文明根脈深長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封面新聞(蔣璟璟):3月31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公布“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最終評審結果。此次十大考古入選項目時間跨度長達13萬年,重要新發現和新成果豐碩,為研究人類起源與演化,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提供科學依據和實物證據。
這里面,四川有兩個項目位列其中,分別是稻城皮洛遺址、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皮洛舊石器時代遺址是國內外罕見的超大型舊石器時代遺址;三星堆商代遺址新發現的遺跡和遺物推進了三星堆遺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禮儀和祭祀體系研究。
重磅榜單,實至名歸。四川兩大項目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既是考古界的盛世華章,更是古老文明穿透時空的璀璨光亮。從稻城皮洛都到廣漢三星堆,從舊石器到青銅器,在巴山蜀水,人類啟智、升維,由野蠻而開化。文明演進的厚重史詩,自遺址發掘現場徐徐鋪展。以此為起點,向前、向后,皆是巍巍大觀。
當我們談論文明,從來都是基于“長度”和“密度”層面的敘事。遠至舊石器時代的稻城皮洛遺址,無疑是關于巴蜀“文明長度”最有說服力的論據。其一舉揭示出七個清晰、連續的文化地層,完整保留并系統展示了“礫石石器組合-阿舍利技術體系-石片石器體系”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過程。夠古老,夠久遠,甚至溯及到了“人類早期智慧發育與成熟”的終極命題。
歷史的長河中,有些文明的火種湮滅無聲,還有些文明的火種,則是星火燎原。至少在巴蜀大地,文明的燭火賡續傳承,千古綿延鼎盛不衰。從稻城到廣漢,“說大也不大”的地方,居然密集發現了皮洛、三星堆兩大讓人嘆為觀止的遺址,這絕非偶然,而是“文明密度”展露的必然。在時間長相續,在空間上相近,這是一種規模化的、連續化的、累進化的高階文明。
文明根脈,源遠流長。所謂文明,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自我啟賦,自我升華,自我認同,自我強化。稻城皮洛遺址、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獨屬于古巴蜀的文明印記,更是華夏民族與中華文明的共有記憶。此刻,串接古與今的大門已然開啟,我們一同溯源而上,一起見證歷久彌新的永恒。
相關報道:四川“雙子星”角逐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評選結果將于今日上午揭曉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華西都市報(記者 曾潔 戴竺芯 實習生 朱翼帆):3月30日,“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匯報會在北京舉行,20個入圍項目代表、考古界專家學者們以“線上+線下”形式參會,匯報展示考古成果,來自四川的稻城皮洛遺址、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雙雙入圍終評環節。
四川“雙子星”能否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將于3月31日上午揭曉。
為助力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今日上午10點,封面直播將帶你走進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改造升級后恢復開放的青銅館,探秘首次展出的青銅神壇,回顧青銅文明發展歷程。
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 出土編號文物近兩萬件 部分造型紋飾前所未見
在30日舉行的“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匯報會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對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發掘情況作了匯報。
三星堆遺址位于廣漢市西郊,地處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積約12平方公里。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是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川渝地區巴蜀文明進程研究》的實施內容之一。
三星堆遺址自1929年首次發現以來,開展了多次考古工作,發掘總面積約1.8萬平方米,遺址的分布范圍、堆積狀況、保存情況、文化內涵、遺存面貌等基本清楚,新一輪的工作重點圍繞聚落考古和社會考古展開。
1986年搶救性發掘了三星堆一號、二號“祭祀坑”,為開展社會考古工作和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線索。時隔34年,三星堆遺址祭祀區重啟發掘。本次考古發掘秉持“多團隊合作”的工作理念,除了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全面統籌負責之外,還有國內39家科研機構、大學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參與其中,共同開展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考古發掘、現場保護和多學科研究等工作。
三星堆遺址的新一輪考古發掘自2020年3月啟動以來,其發掘成果持續引起社會關注。此次共計發掘面積1202平方米,發現“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溝55條、柱洞341個、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區的分布范圍和內部布局。截至日前,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已出土編號文物近兩萬件,扭頭跪坐人像、青銅頂尊人像、神樹紋玉琮等器物前所未見,引發社會關注。
談及三星堆考古取得的成果,雷雨說,新發現的前所未見的遺跡和文物,進一步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也將深化關于三星堆文化遺跡古蜀文明的祭祀場景和祭祀體系的研究,彌補以往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三星堆遺址三號“祭祀坑”出土的頂尊跪坐銅人像和銅圓口方尊等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國內其他地區文化的因素,進一步實證“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考古發掘運用了“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新理念,創新使用了現代化多功能保護平臺、恒溫恒濕考古發掘艙、現場應急保護實驗平臺、多功能考古發掘操作系統、遠程控制系統、不間斷高清數字記錄系統等,推動了田野考古方法和手段不斷進步,對中國的田野考古意義重大。
稻城皮洛遺址 實證13萬年前古人類已頻繁登上青藏高原
與此同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研究所所長、皮洛遺址考古發掘執行領隊鄭喆軒也對皮洛遺址的發掘情況作了匯報。
2019年開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相關團隊在川西高原開展舊石器時代考古專項調查工作,在甘孜州新發現40余處海拔3000米以上的舊石器地點。2020年5月,考古隊在稻城縣附近發現皮洛遺址。
皮洛遺址位于稻城縣金珠鎮七家平洛村,距縣城約2公里,海拔約3750米,處于金沙江二級支流傍河的三級階地,整體面積約100萬平方米。
本次發掘揭露出多個古人類活動面,出土編號標本7000余件。連續的地層、豐富的遺物說明遠古人類在此的活動頻率和強度非常高。根據目前的測年研究,皮洛遺址第三層地層年代不晚于13萬年前。這意味著,至少在13萬年前,古人類就已頻繁登上青藏高原。
根據地層關系、堆積特征和遺物發現情況,可初步將7個地層的發現分為三期,整體構成了一個罕見的舊石器時代文化“三疊層”。7個連續的文化層,完整保留、系統展示了“簡單石核石片組合-阿舍利技術體系-小石片石器和小型兩面器”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過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國西南地區連貫、具有標志性的舊石器時代特定時段的文化序列,為該區域其他遺址和相關材料樹立了對比研究的參照和標尺。
并且,遺址發現的手斧、薄刃斧等遺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遺存,也是目前東亞地區形態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組合,為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莫維斯線”論戰畫下了休止符。
同時,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遺址填補了東亞阿舍利技術體系在空間上的一個關鍵缺環,串聯起東西方阿舍利文化傳播帶,對于認識亞歐大陸東西側遠古人群的遷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義。
相關報道:舊石器考古就像“盲人摸象”摸得越全認知越多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戴竺芯 曾潔):看上去略顯荒蕪的稻城皮洛遺址,為何能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對此,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專訪了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舊石器時代考古專家高星。
在高星看來,皮洛遺址能獲得評委的一致認可并入選,取決于其毋庸置疑的獨特學術重要性和社會意義。無論是遺址巨大的分布面積,令人嘆為觀止的完整地層序列,還是出土遺物的豐富、獨特和組合特征,都令業內的學者驚嘆和欣喜。他說,皮洛遺址揭露出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過程的重要歷史篇章,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國西南地區連貫、具有標志性的舊石器時代特定時段的文化序列,填補了該地區乃至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一項空白,對于遠古人群遷徙、融合及文化傳播、交流路線,以及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等系列重大問題提供了關鍵信息。
“舊石器時代占了人類歷史上99%的歷史進程,是人類最為基干的部分。”高星說,這一時期的遺物遺跡看似簡單,實際上卻孕育了后期人類社會各方面的元素,因此其重要性不可忽視,皮洛遺址的發現正印證著它的重要性。
對于皮洛遺址接下來的發掘和研究,高星希望能更加深化和細化,包括遺址年代的進一步測定、目前缺失材料的新發現,以及目前已提取樣本的深入研究。
“皮洛遺址目前發掘和調查的面積仍然有限,下一步可以繼續擴大調查和發掘。”高星說,舊石器時代遺址與歷史時期時代遺址不同,由于當時的人類處在狩獵、采集,不斷遷徙移動的狀態,因此很難存在集中的遺物遺跡和相關記錄,其文化遺存常散布在一些區域,遺址范圍或許更大。“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和發掘就像‘盲人摸象’,摸得越全,得到認知越多。”
相關報道:皮洛遺址為研究早期人類遷徙提供豐富材料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戴竺芯 曾潔):3月31日,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分屬史前考古類目的稻城皮洛遺址位列其中。該遺址被譽為一次具有世界性重大學術與社會政治意義的考古新發現,2021年9月正式對外公布后,可謂“石破天驚”,備受關注。
稻城皮洛遺址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法寶”是啥?接下來又將如何發掘?記者專訪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研究所所長、皮洛遺址發掘執行領隊鄭喆軒。
對研究早期人類東西方文化交流 提供關鍵性證據
“每一個遺址都有獨特的重要性,皮洛遺址成功入選的‘法寶’是基于它的重要學術價值,以及所涉及的系列重大學術問題。”鄭喆軒進一步解釋,比如遺址高海拔的地貌環境背景,為研究古人類何時、以何種方式征服和適應青藏高原高海拔極端環境等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
鄭喆軒說,遺址所處的青藏高原東麓歷來是人類遷徙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走廊,遺址連續反映的至少三個不同石器工業面貌的文化層,究竟是古人類為適應環境所作出的選擇,還是不同人群帶來的不同技術,或者說多種因素的疊加影響,這為研究早期人類遷徙、擴散等問題提供了豐富材料。再如,遺址發現數量豐富且制作精美的西方阿舍利遺存,對研究早期人類東西方文化交流、阿舍利技術傳播路線等問題都提供了關鍵性證據。
“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我們很高興,意義十分重大。”鄭喆軒說,首先,這是一種肯定,“是對我們曾經生活在皮洛遺址的先民們頑強而偉大的生存發展史的肯定,是對皮洛遺址本身所包含的相關重要學術價值、學術意義的肯定,也是對我們團隊辛勤工作的肯定。”他認為,皮洛遺址的考古工作對四川地區舊石器時代考古乃至一定程度上對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都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也為遺址所在的稻城縣、川西高原增添了一張靚麗的文化名片,有利于當地文化旅游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不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皮洛遺址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對于考古隊員們是一種鞭策。“皮洛遺址的工作其實剛剛開始,目前僅第一個年度的發掘工作就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收獲。此次入選鞭策我們要更加努力地做好遺址長期發掘、研究、保護、利用工作。我們也將開展更科學系統的發掘,并爭取有新的發現和突破。”
第一階段野外考古已結束 目前正在整理資料
鄭喆軒介紹,皮洛遺址第一階段的野外考古工作已于2021年11月結束,目前正在進行資料整理的關鍵階段。出土遺物方面,目前正在進行石器整理工作,包括石器拍照、繪圖、測量、統計分析等一系列工作。遺址環境考古、年代學、古DNA等多學科工作,各個團隊也正在有序推進。同時,考古隊也在為今年的發掘及遺址未來長期的保護和利用做一些前期的準備。
目前,通過系統的整理工作,考古專家已對皮洛遺址的石器類型、操作鏈模式等文化面貌有了更加清晰明了的認識,遺址年代、環境方面也有一些新的進展,對古人類對高原環境的適應性行為研究也更深入,這些工作最終都將以完整的學術論文形式來呈現。